“复旦导师制计划”系列讲座之《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
5月23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引驰来到上中,为复旦导师计划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堂题为“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讲座,向同学们展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唐诗。
陈教授的思维非常缜密,对于问题的考察也颇有逻辑性。在表现唐诗的与众不同时,使用了对比的方式,在宋词的世界里是离不开“情”的,无论哪首词作,什么历史背景,最先吸引读者目光的都是情感。不仅如此,宋词追求的还是一种“理”的表达与展现。而唐诗则远非如此,诗歌的本身就能揭露出很厚重的历史背景,在题材上,也各有千秋。教授时以大家熟知的诗歌《过故人庄》为题,时又以大家所不晓的《赠李白》为例,把丰富而多彩的唐诗画卷呈现在了大家面前。
接着,陈教授就着唐诗中无所不容的亲情、友情、边塞、山水等题材,分析了其背后的根源理由。唐代总体是一个大时代,不仅是国土大,更有人种多,交往广,文化多元之奇。前溯魏晋,九品中正盛行之时,唯贵族可官;后视两宋,唯有平民科举可官,处之其中的唐代,就汲取了各色的特点,造就了纷繁多彩的唐诗世界。如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他们每个人的身世都是那么的不同,随着教授的阐释,大家心中的谜团也渐渐散开。
此外,教授还为同学们提供了不少解读唐诗的方法与技巧。例如声韵断句,意象的把握,很多都是大家前所未知的。在当下的语文学习中,不少同学有不少问题不解,也踊跃提出与教授进行讨论和交流。陈教授从文学的广度对此进行了回答,很好地解释了大家的疑惑。
文学诗赋是天马行空的,谈论之时,却也要十分严谨。陈教授将做文学的精髓与思想也一并授予了大家,课后,大家纷纷将掌声送给了教授,这堂博古通今的课程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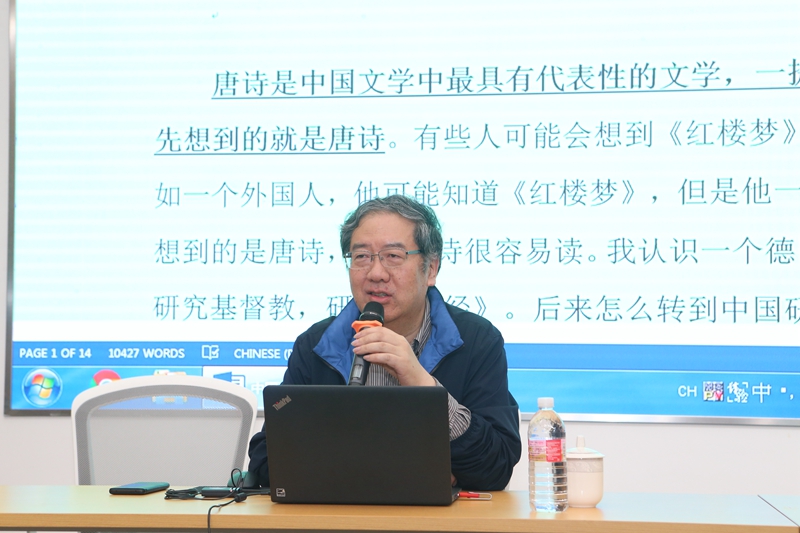


(撰稿:高一(10)班郭诣丰\摄影:狄确\审稿:胡晨)
“上中-复旦导师制计划”化学微课程——《醛、酮、羧、酸及共衍生物》
2021年5月23日,来自复旦大学的孙兴文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第4次微课程——醛、酮、羧、酸及共衍生物。孙教授首先从上节课醇的氧化讲起,讲述了乙醛和银氨溶液反应产生光亮银镜的反应,通过对这一人尽皆知的课内经典反映的深入讲解,孙教授使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简单现象背后的复杂机理问题,以及有机反应的魅力与奥妙。
接下来,孙教授就今年等级考中涉及的有机反应中的“保护”步骤作出了阐述,孙教授破除了同学们对于双键保护的粗浅甚至错误的认识,辅以具体的实例来加深同学们对其真正化学机理的认知。孙教授提出了“保护”的几个特点:呼之即来、来完就占、占完就走。他以国际时局作喻,使同学们在哈哈大笑中明白了道理。
最后,孙教授以其标志性的人文关怀对我们聊起了药业中的剂量问题和虚假广告宣传,通过对多酚的知识讲解,孙教授解释了茶多酚并不能抗衰老的原因。通过对退烧药的化学本质的剖析,同学们认识到了体内代谢对药品毒性判断的影响。课程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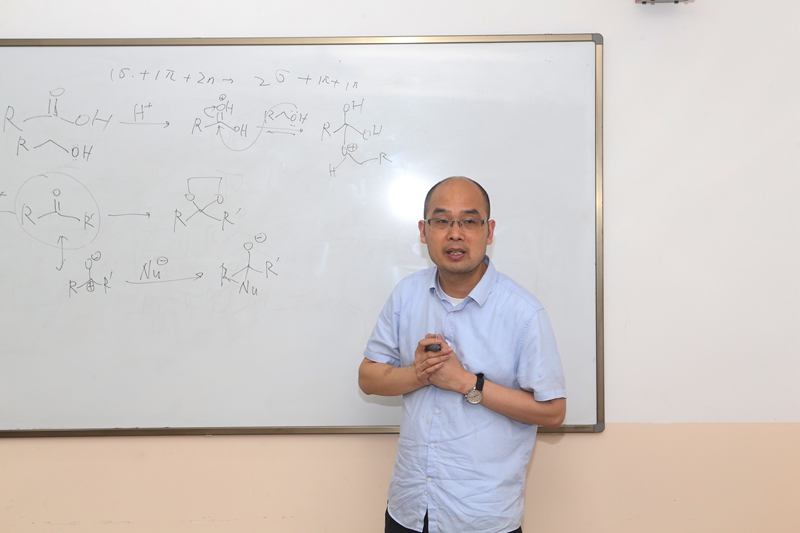

(撰稿:高二(9)班薛志恒\摄影:狄确\审稿:胡晨)
“上中-复旦导师制计划”生物微课程——《科学之美》
2021年5月23日,高二部分同学在工程楼二楼进行“科学、艺术与创新思维”的课程。卢宝荣教授介绍了本节课程的第一、第二组分享的主题,随后进行了每周一歌的分享。
第一组同学介绍了国内外一流大学校训的分析比较。徐嘉澄同学介绍了清华、北大、复旦、交大、同济等国内知名高校,以及哈佛、麻省理工、斯坦福等国外知名大学,并进行了生动的对比分析,中国从传统教育出发,更强调“德”;要将自己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结合;要不断学习、思考。国外大学的校训更追求自由和真理;崇尚动手实践;有宗教意义。卢教授带领同学们作了比较,引导同学们更深刻地思考,看待这个问题,短暂的休息之后,第2组介绍了达芬奇。林昱晴同学以一个有趣的小视频开场,吸引了同学们的注意。之后对于达芬奇的生平介绍也生动而吸引人。
本节课两组同学都展示了精彩的分享,之后卢教授也拓展主题,引导同学们进入“群论”,共同探索这个命题下的一切科学与艺术之美。


(撰稿:高二(3)班 应玥\摄影:狄确\审稿:胡晨)
“上中-复旦导师制计划”物理微课程——《自然科学的起源》
5月23日,来自复旦大学的盛卫东教授继续上次的讨论,向同学们进一步介绍了自然科学的起源。
盛教授从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说起。在给出自己的回答前,他先给出了三个简单的问题:“科学是什么”,“科学如何萌芽”以及为何未能出现在中国。接着,盛教授介绍了自然科学出现前人类对于自然现象的认知和理解,指出宗教是人类认知自然的重要方式,并比较了各个古文明的宗教。从犹太教开始,盛教授进一步讲解了一神教的出现以及进一步的演化,包括发源自犹太教的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之后他点出介绍宗教发展的目的:宗教即认为自然是神力量的展示。接下来盛教授开始介绍从宗教到科学三千多年的缓慢转变。他先介绍了物理是要用一套规律解释自然现象,并指出其与单一神教认知的“自然现象由单一神力量支配”的某种相似性,并认为中国文明未产生科学是由于我国古代宗教文化不认为“单一规律”的存在。盛教授将自然科学也视作一种信仰,而它和宗教的区别在于宗教无法证实或证伪。解答了第一个问题后盛教授开始介绍科学如何萌芽。他将科学萌芽的过程比作宗教信仰的建立过程。正如宗教信仰由“神迹”而起,科学由描述现象的简洁公式而生。而天体物理学的简洁现象构成了初始物理学的“神迹”。由于时间关系后两个问题盛教授还未来得及作出解答。


(撰稿:高二(9)班陈修安\摄影:狄确\审稿:胡晨)
“上中-复旦导师制计划”数学微课程——《无理数的发现与实数系的建立》
5月23日,复旦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楼红卫教授为我校高二学生开展了第四次数学微课程。
楼红卫教授先从熟知的勾股定理讲起。勾股定理最早出现在西汉的《周髀算经》之中被认为是公元前十一世纪的商高首先证明。由于年代久远,商高是否为真实历史人物不得而知,而同学们能确切知道的是三国时期吴国的赵爽不仅正确证明了勾股定理,还为《周髀算经》作了注。《周髀算经》中原有《周公弦图》来解释的勾股定理,无奈失传。赵爽也画过弦图,亦失传。三国魏的刘徽用另一种方法证明了勾股定理,无奈他的图也失传。不过后人根据其文字描述,均大致还原了这些弦图。《周髀算经》绘出勾股定理求同地距离的方法,但可惜作者未意识到地球是球形的,导致误差较大。唐代的一行和尚用此法测得同地距离,与今天差距较大。勾股定理在国外被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因为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发现了勾股定理,但其实,古巴比伦人再早于其一千年时便发现了该定理,而今天人们经过研究普遍认为毕达哥拉斯并未证明勾股定理。欧几里得在《几何原本》中则确实给出了严格证明,但他比毕达哥拉斯晚了两百年左右。
楼教授由此引出了第一次数学危机。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任意两条线段都是“可公度”的,即存在另一条更短的线段,使两条线的长度均为其整数倍。但其学派的希帕索斯在研究正五边形时敏锐地发现:若正五边形的边长与对角线长“可公度”,把它们都视为整数,则将其对角线互相交出的五个焦点相连得到了新五边形,其边长小于原五边形,而其边长、对角线长可算出也是整数。如此不断进行,则任意次这样操作后得到了任意小的“整数”,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此惊人的发现却遭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大力打压,因为无理数会推翻毕氏数学体系的根基,且无法重建这样一座宏伟达大厦,从学术与政治两方面来说都对毕达哥拉斯学派不利,为解决这一问题,公元前四世纪左右的欧多克斯引入“比例论”,首先跨越了有理数的天堑。他称两个相同的量(如都是长度)之间可定义“比例”,这些“比例”可以进行大小比较。遗憾的是,他并未认识到“比例也是数”的一种。这样的理论持续了约两千年,直到19世纪左右,戴德金提出了实数的概念。
与整数、分数不同,实数难以用具体事物来描绘。可以说实数是人造的。并且不同的人可能造出不同的“实数”,因此一个标准是需要的,为更好保留性质,实数应可以比较大小,进行四则运算,并且数量要恰到好处,不能过多。除了基本性之外,有理数还具有稠密性(任两个有理数之间有有理数)与阿基米德性(总可以找到一个给定正数的某整数倍大于另一个给定的有理数)。有理数集是一个全序集,具有三歧性(其中任意两数都有要么相等,要么必有一个大于另一个)。希尔伯特提出实数系公理,指出实数是一个域:满足加法交换律、结合律,存在加法单位元,存在负元;满足乘法交换律、结合律,存在乘法单位元,非零元具有逆元;满足乘法分配律。进一步,他提出了与序有关的序公理,指出加法与乘法有保序性。同时,实数也具有阿基米德性,且是完备的(若有另一个集合是实数集的超集,且满足上述所有性质,则其只能是实数集本身)。而戴德金的实数构造如下:取有理数集的一个非空真子集,其无最大元,且有理数中不存此集合中的任意数均比该集合中的任意数大,则称该集合为有理数集的一个“分划”,若它的余集中无最小元,则称其为“无理数”,否则称为“有理数”,即给了新的有理数、无理数定义。“无理数”是存在的,因为它的余集无最小元,可用取一个更小的(用稠密性)来构造。之所以不用“无限不循环小数”来定义,是因为其做加法较困难,尽管比大小会方便。戴德金的定义中,“有理数”与原先认识的有理数是一一对应的,因此可通用“有理数”集是“加群”,是“域”。在此基础上,可定义“实数”集的加法、零元、复元等,从而构建出严格的实数体系。
楼教授上课风趣幽默,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高深的数学思想表述出来,并讲了许多历史故事。既为一些发现提供背景,又激发了同学们的兴趣。在这节课中,介绍了勾股定理,无理数的发现与实数体系的建立,内容看似简单实则深奥,楼教授把这些知识讲解的十分透彻,使同学们受益匪浅。


(撰稿:高二(8)班 马添翼\摄影:狄确\审稿:胡晨)